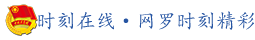《秉烛行吟》散文集作者林遥
一、说书人
他身穿整齐的大褂,一袭民国时的长衫,浑身透出精、气、神,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桌上一块醒木、一把折扇、一块手帕。醒木一拍,众人听书。评书、评话、评弹......斗转星移、龙蛇起陆、好汉且留名姓!口声,口授,口耳相传......月黑风高、刀剑无眼、诸位莫要惊慌。你可听好了......故事充满天机与神明。
北方称“评书”,南方称“评话”,今日之北方评书,即“北京评书”。听书,是用耳朵听说书人讲故事。林遥说书扶危济困,忠义侠胆,时而婉转凄艳,时而慷慨激昂。林遥说书引人入胜,趣味盎然,如同苏轼言:“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如同他写的《庚子杂诗》:“春雷惊起蜇龙醒,一夜声声溢耳听。纵使海潮来作雨,至今疑有怒涛声。”
这位说书人林遥,本名郭强,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延庆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位说书人不但说书,还写了《说书人》(载《青年文学》2020年第9期),后将此文收入了乔雨主编《妫川文集》中的《秉烛行吟》一书。
《尚书.洪范》:“听曰聪,聪作谋”。听书有诸多好处,节省视力,缓解眼睛疲劳。可以心有二用,听书同时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有趣有味,收获良多。听书可以学习发音,与人交往表达能力更强了。说书人,对于现在来说“昨天”,而今天对于未来也是历史上的“昨天”。评书满足了社会娱乐需求。彼时,人们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评书有猎奇、打斗、人情,也有托古言志,而非真说历史。“礼失求诸野”,说书,即为“野史”。虽是“野史”,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积淀,无论时光流逝,世事变迁,总会带给听者魅力,带给听者自信与光荣,创造今天新的文化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明天的历史。
传说,“评书”的历史上溯到东周。评书行当供奉祖师是周庄王,说周庄王传下一把宝剑、一道圣旨、一方大印,演变为说书人演出的道具:扇子、醒木、手帕。林遥在《说书人》一文写道:史料考之,唐朝时出现“说话”,与评书表演形式相类,至宋代,又有进一步发展,有了各种“话本”,让“说话”更为精彩生动。“话本”既是说话人的底本,亦是中国小说源头之一。“评书”与中国小说,相伴相随。
林遥用语言替代文字,把自己的知识和人情渗透进一部书的情节,且研究透彻。犹如历经洪水之后,能归于世间最初的本源。我的岭南文友闲云野鹤先生,曾创作古风一首《冬池言荷》:“未出污秽气先清,淡雅脱俗自生成。冬逢青帝求得允,只留半篷世太惊。”此古风送给说书人林遥,林遥说书犹如《桃花扇》中的柳敬亭,丈夫气概,人品高绝。
林遥自幼喜欢听评书,从收音机到电视机,只要有评书,几乎没有落过。14岁,第一次学着登台说书,觉得这个行当,太不得了,迷得不行。没有少年时代的愚痴,亦不会有今天说书写书的老道。可是评书终究还是没落了,在互联网遍布娱乐信息和资讯的今天,评书应该怎么说?林遥在《说书人》一文写道:
二〇一五年,我尝试着恢复现场评书演出的形式,书馆定名为“凭书馆”。取个“凭”字,凭的不过是对评书的热爱。在“凭书馆”演出的说书人,已然不再专职说书,我的师兄弟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有餐厅的经理,也有后灶的厨子,有电台的主持人,更有影视演员。他们过来说书,只是因为爱着评书。
从未想过,有一日,说书人竟然成了理想主义者。二〇一五年八月的一天,只有一位观众来听评书。我没有抱怨,醒木一拍,对着他说了一个小时。散书之后,我向他鞠躬:他若不来,我当天的书都开不了。
要想说长书,就要多阅读、深阅读,读懂人情世故。当代的人情世故是什么?一是,人们重视物质生活的品位,有温度的品牌精神将成为新的消费需求。二是,人们重视金钱之外的东西,比如健康、爱情与家庭,愿意在工作之余抽出精力陪自己喜欢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事。三是,人们开始自觉反省人生意义,寻求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无限的人生价值,试图寻求灵魂的苏醒。你懂得了社会还不够,还要用你的一张嘴表达出来,把书说好,这才是有意义,自觉寻求灵魂的苏醒。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那里去?要想说好书,就要考虑到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林遥选择了说《西游记》。既然单纯依靠故事,没有办法吸引人,那就讲一个大伙儿熟悉的故事,看看如何能说出新意。林遥在《说书人》写道:
通过阅读《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说书时,把历史真实的三藏法师的故事杂糅其中,给予三藏新的面目。我甚至将《西游记》以十四万字的篇幅进行了缩写,出版了一套《降魔修心:彩绘西游记》。五年时间,我的《西游记》系列评书时长已接近一百六十个小时,但故事刚讲到原著的第五十五回。听我评书的一些孩子,已从小学升入初中。说书时,我承诺在他们上大学前,一定将《西游记》结束,说这句话的时候,底下哄堂大笑。
让人欣慰的是,眼下,人们虽然“读”的书少,但是“听”的书多,听书却成“新主流”。全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成年国民和未成年人有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今天的知识付费节目,如同当年的评书,正在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
林遥开始步入知识付费领域,讲解《金瓶梅》。《金瓶梅》的小说没有办法改编成长篇评书,因其中的故事过于琐碎和生活化,情节不够起伏激烈,然而《金瓶梅》的文学价值毋庸置疑,其自然主义写法,已属现代文学的思考,对国人生命底色的揭示,至今仍然有意义。那么是否可以尝试借鉴评书的技巧和讲述方法,来展示《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呢?宣永光先生在《妄谈疯语》一书中说得好,中国古人的作品,是因为和平劝解、引人向善,甚至一些淫书艳史,也含着“劝善”的用意。而今人现代文明书,大多没有“开导化解”的笔力,“诲淫”只能引人纵欲,“挑拨”只能动人愤争,使人霸道。古圣人的学说,安慰老实人,警戒野心人,读后减少兽性,使人步入正轨,所以得到大众百姓的崇拜。古时的书重克己,所以学者多正士,现在的书重责人,所以学者多不被人尊敬。
我为什么欣赏林遥《说书人》?《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立文之道有三:一形文,五色是也。二声文,五声是也。三情文,五性是也。而“情文”是最重要的.是最真实的,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林遥的作品有看头、有听头、有嚼头。撰写的“我的故乡,我的文学”情溢于表!其文字散见于《文艺报》《北京文学》《钟山》《西湖》等报刊。出版有长篇小说《京城侠谭》、散文集《明月前身》《非主流的青春》、诗集《侠音》等。
听书,能让听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林遥和他的师兄师弟们“说书”,而我们去听书,是尊重传统美德的行为。尊重传统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一直被推崇的美德,重要原因在于其有助于保持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平衡稳定。如果这种对传统的尊重被称为“保守主义”的话,我觉得“保守”非但不该受到鄙视,而且应当格外小心地珍惜。有继承才有发展。那么,我们应当“守”的、“保”的是什么呢?“中国文化精神,至少在这一点上,实有其至高无上之价值。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是也”(唐君毅语)。
我读了林遥的《说书人》,便想起了我的重庆文友义玄子在《中华文化正观》一文所说:古有黄帝问道于岐伯,尧、舜、禹开疆拓土,分封禅让。圣贤入世,顺应天地运行之道,秉承自然造化之功,姜太公渭水垂钓,得以重用,辅佐周文王开创大周八百年盛世基业,彼时盟国相庆,万邦来朝,实乃中华文化昌隆之源泉是也。
《说书人》来自于对传统美德的历史继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在儒家思想化育下形成了悠久的传统道德。《左传·襄公十年》有人生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立德”放在人生三大价值的首位。孔孟所开启的儒家道统始终把道德实践看作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途径。说书人抛弃的是:儒家思想的糟粕,其时代的局限性。说书人继续的是儒家道统:仁爱、中和、公忠、正义、孝慈、宽恕、谦敬、诚信、礼让、自强、持节、明智、知耻、勇毅、廉洁、勤俭、节制、爱物......为的是使当代社会减少暴戾,增其和美。
林遥的说书,让我有了“三气”:充满豪侠之气的《史记》、充满雅稚之气的《世说》、充满狐魅之气的《聊斋》。有此三气,足以抵挡当今世之俗气,足以抵挡当今世之偏激气也。《说书人》一言一弊之:中华文化是中正合和文化,不是犬儒奴役文化。中华文化是君子精明文化,不是暴行流氓文化。
二、守庙人
“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林遥在“说书”与“写作”之间转换着。他在《秉烛行吟》书中写了《守庙人》:“吾乡的村里有一座庙,位于庄子的正中心。站在庙前眺望,晴天时可以看到四周的高山和白雪。庙里有神灵的塑像,两壁涂绘有各路神道、释道,然而色彩多已斑驳......”
守庙人守的是什么?守的是一种信仰!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信仰。不论信仰的是宗教,还是文学艺术、科学哲理,人是因为有了信仰方显出“存在”的意义来。而信仰的本质是自主的、多种的,并不特指某个唯一教派,也与当代意识形态无关,更不能拿科学与技术来检验。人生信仰是一种慰藉和力量,人生信念是对真善美的寻求和对人生价值的思索。
撷一片旧时月色掌灯,林遥在《秉烛行吟》一书中的“跋”中写道“文字之于我,更是生命的一种诉求与展示,心灵的一种寄托与宣泄。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书自己能书之情,达他人未达之意。这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认认真真坚持写作的原因。”。
作者与他写的《守庙人》一样,说实话、讲良心、做好人。守庙人守的是什么?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终极关怀。从《道德经》“人之大患,在吾有身”的思考,到《红楼梦》“警幻仙境”对人生的咏叹,对“人性”的思考。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终极关怀的丧失,则意味着全社会的价值信仰的失落,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深层链条的断裂。反思近代史,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等人都曾有过终极关怀,他们的探索虽然在当时受到冷落,却是符合人文精神的。近代康粱以来,一直是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牺牲了学术的独立品格,酿出一幕幕的悲剧,发展至顶峰,乃是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姚文元摇身一变,成为敲打文化人的一根棍子,成为最令文化人寒心的“锦衣卫”。到了近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躲进小楼成一统”,为学术而学术,政治与我何干?百姓的苦乐与我何干?人文科学,如果不把触角伸向当下的民众生存状况,那么他便是纸上的学问、死的学问、背弃了他自身责任的学问,如有清一代的干嘉之学。
守庙人因信仰而高贵:守庙人守的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守庙人识字,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每次诵经时,他的面部就开始活络起来,进而沉静,然后恢复如常。守庙人能写字,写大字。庙院里的锄头把、墙壁上常见浓亮黑圆的大字,间架工整“(摘自《守庙人》)。
守庙人守的是“人学”,讲究“内在的人文主义”。这种“内在的人文主义”是人与万物同流,与天地相合的关系,构造出一种“终极”的精神信仰。在林遥《秉烛行吟》书中,有诸多篇章,如《氍毹忆朱痕》、《乡关写意》、《江南酒意》、《寂寞梨花魂》、《上善若水》、《武侯之困》等文章,体现着“内在的人文主义”,对历史的文化典制、社会价值、道德规范、礼仪习俗等方面,均有涉猎。2018年,林遥在全国青年作家笔会发言:一个关于悲欢离合的故事,可以帮助一个人从焦虑和困惑中走出来,这就是文学的魔力。好的小说其实记录的是世态百相,传承的是人类情感和记忆,是我们心的困难,情的困惑,是我们人生的种种境遇情景: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希望与绝望。
传统的“人文精神”,是当代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有这样的特征: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有理想的人。中国古代对人与人之间基本的道德规范称为“人伦”,亦称“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左传》释义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两千年来的国人,一直强调用它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中国被世人称为“礼仪之邦”,直到“文化大革命”,这种“人伦”关系遭到了全面的否定,引起了人伦混乱,是非颠倒。
林遥说,我也许只能在冰冷的文字里,寻得救赎,寻得生命最大的慰籍。“数年的时间,我步履蹒跚,看过了散落在京郊周边大小散落的数十座残存戏楼,蓦然想起自己写过的《风雪山神庙》中的诗句:我静候在台下,等待散场。只记取戏中箫声低咽,锣鼓冰凉。”见林遥《氍毹忆朱痕》一文。
阳光是柔和的,月亮是清秀的。林遥虽有“箫声低咽,锣鼓冰凉”的文字,但纵观《秉烛行吟》一书,我看到的更多是,他在寻吟一缕清纯的空气,携一颗灵魂自由散步。如同作者所说,中国的文字就应该是美的,失去了美的特质的文字不是好文字。一篇好的文章一定要让人感受美,感悟美,渴望美。
作者写的《守庙人》是一座小庙,而宝鸡市岐山县有座大庙,即“周公庙”。周公,姓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制订礼乐,建立朝纲,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被尊为“元圣”。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后世公认: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曹操叹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令天下归心。作家陈忠实在周公庙有题词:“周公之哺乃兴邦佑民之思想方略以及道德人格,为后世一切想成事立业者之楷模。”而林遥“唯愿采撷一片旧时的月色,在心中掌灯,将笔下的一字一句,写得活泼而有风致,于愿足矣”。
《秉烛行吟》一书,让我读到了作者:遵循周礼,依中道而行,走中庸之道,无过亦无不及。
三、取经人
《秉烛行吟》的人文精神是一束希望之光,让生活有了阳光。在林遥看来,人生的旅途中,每处山河都是自然的造化,每片白云都是人文的感悟。
濯长江之清流,捧西山之白云。观赏形胜,旷达乐观之胸襟。苏辙主张,“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强调后天的学习和修养,亦包括游历,欣赏自然山水。《秉烛行吟》中的诸多篇幅,如《丝路南国有于阗》《阳关独唱》《沙中清泉》《天人绝构莫高窟》《春风不度玉门关》《风吹戈壁滩》《玄奘的背影》,记述了作者游历山水,超然物外,消解苦恼,增加乐观情绪的所思所得。
跋涉行路易,文化守护难。林遥行走中国,记戏楼、望胡杨,闯关玉门、观窟敦煌,拜水都江堰、醉梦入扬州,南长滩纷扬梨花、古于阗金玉佛国,构成《秉烛行吟》21篇历史文化散文,是作家寻追记历史人物的背影,诠释文明的兴衰,感叹文化的坎坷。在探幽发微、述往思来中,蕴藉着对传统文化的追思。
《玄奘的背影》记述了一个取经人的故事:“这位僧人,法号玄奘。他的一生,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十七年的时间里,行走五万多里,追寻佛法的真谛。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十九年的时间里,笔耕不辍,翻译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字。”
取经人的故事让林遥神往,取经人的故事让作者“学而后创”。费孝通先生曾提醒国人,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道路,我们需要补课。如果没有人文学术的繁荣,文化仍将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而要取得人文学术上的成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学而后创”,先“衔接上世界性的文化”,再有所创新和突破。是的,应像玄奘一样去取真经。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为了衔接上世界性的文化,“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这是玄奘西行前立下的誓言。贞观元年(627),29岁的玄奘独自一人,踏上了远赴印度的取经之路。玄奘右手执拂尘,左手捏佛珠,背负佛家弟子专用行囊,行囊顶部有一个遮伞,起到挡太阳和避雨的作用,囊顶有一盏小灯,垂落于他头部。自从上路,这盏灯就一直亮着。它的实质作用是供佛之意,在多少个黑夜和茫茫大漠中,它又成为玄奘不泯的信念之火。在玄奘西出长安后不久,朝廷就发出了让沿途县衙捉拿他的命令......
佛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竟然让玄奘勇往直前,誓不罢休。梁启超概括:“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独善,是住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去驳斥佛教的荒谬,不会再去附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佛教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有包容、有平等,有精进、有布施。在今天这个物质欲望膨胀的时代,佛教所倡导的慈悲、平等、善良、宽容、多元、和平等价值观,无疑是对治社会人心的一剂良药。保持纯朴善良本性,重新走向传统之路,国人重拾信仰的时代已经到来。
《天人绝构莫高窟》一文中,追述了唐人的坦荡胸襟与生命的活泼自由:我始终记得第四十五窟的菩萨像。这个洞窟开凿于盛唐,彩塑的菩萨体态婀娜、丰盈健美,肌肤莹润细腻,面相年轻。即使在昏暗的光线里,即使在一千二百多年过后,我依旧能感觉到它肌肤的弹性。它恬静慈祥的神情、开放的胸襟和腰胯轻薄的罗裙,都传达着盛唐时代的气质。
可以说,人类轴心时代的“因”,造就了后来强汉盛唐的“果”。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相继出现了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分别提供了三种伟大的学问。这些思想家出现在三个民族之中。一个是希伯来民族,提供了神学。第二个是希腊民族,提供了哲学。第三个是中华民族,提供了人学,或称之为人文,或称之为人文精神。他们贡献了全人类文明的种子。林遥的《挑灯看剑,武侠小说史话》从始至终,贯穿了人文之侠气。
春秋战国时期是原创性文化的形成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初的基本论点。《周易》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季节、时令变化的学问,“人文”则是“文明”的同义语。是的,我们的文明衰退了。作者在《阳关独唱》一文中写道:“站在墩墩山下,面前就是丝绸古道,举目四顾,天苍苍,野茫茫......我能听见历史在脚下呻吟的哭泣声。”
是的,我如同林遥一般,怀思古之幽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学问的最高境界诚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唯有敢于孤独者,才有自信心和定力,也才具有挑战性。这种自信心和挑战性,正如汤恩比所说,乃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未来文化的创造性,寄托在敢于孤独、耐于孤独者的身上。独立之精神是文化人的灵魂与生命。
真正的文化人戒浮躁、多自谦,胸怀平常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土服,冷眼观察人生百态。真正的文化人各自孤立, 如“一盘散沙”,不受外界干扰,真诚地写出传世之作来。真正的文化人像天上的星星各管各, 各自发光,不侵犯别人,也不被侵犯,越是无求于人越是自主自在。
林遥曾经赠送诗集《凭栏迎雪阁诗词》于我,其中有“转世须经三界准,轮回莫问未来身。我如长剑兮名酒,照破青天对鬼神。”这让我想起了一副对联:黄老思想,出世入世无为妙化;道家精神,独善兼善顺应自然。澄心明物,谦卑对待天、地、人;和光同尘,执笔呼唤远古文明。林遥有微信公众号“林遥论剑”,大家可以在手机上看看,什么是现代版的人文精神。众人如果能够全面地继承老子,墨子、孔子的思想来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吗?
百家争鸣形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活跃局面,构成中华文化中的原创性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融通。东汉佛祖西来,佛教与中土文化融洽,产生了不同于印度的中国化佛教,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大融通,形成了儒、佛、道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中华兴盛千年。
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的西学东渐,百年来中西文化的碰撞,呼唤第三次文化的大融通(中西文化的融合),期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掀开了中国历史的一角,全景地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百年中由于经济模式转型失败和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带来的类似于“锁定死亡”的后果。迈向现代文明,其路径是“中西文明融合”,黄仁宇先生称中西文明融合是中国最大的事。第三次文化的融合融通要有玄奘的气魄,为取真经直到生命的终结。“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别看车轮滚滚,我们其实也就是在追寻玄奘的背影罢了”。
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了工业,没有完成工业化;吸引西方文明,没有消化融合,仍处于对撞对抗中。走向未来世界,要转型转轨,但,何其艰难!“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说这话的人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他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他死于1939年,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之日。
儒学又被称为“为己之学”(身心性命之学) ,因有“古之学者为己”之说。这里的“己”,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所显现的中心点。要完成自己的人格,也就关系到要发展他人的人格,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负责。《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通过身、心、灵、神这四个层面逐渐深化,来完成个人人格的。这种个人人格完成的过程,始终贯穿着慎独精神。《秉烛行吟》“跋”:唯愿采撷一片旧时的月色,在心中掌灯,将笔下的一字一句,写得活泼而有风致,于愿足矣!
走回人间正道,重归社会清明。《秉烛行吟》散文集,是一本人文精神之书,“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一本耐读可品之书,“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唤醒古书一缕香,我感受到了林遥力聚笔端的功力,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本。
林遥写七绝.《参禅偶得》““一身如在乱山间,叠叠重重已倦攀。过了一山还一望,依然满目是青山。”《易经.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之者林遥,秉人文之烛,善也;成之者林遥,行圣贤之吟,性也。我期待着,并坚信有《玄奘的背影》中的“取经人”!
注:本文参考了:石中元.著《文苑撷趣——打捞我的笔墨生涯》第十章人文精神散论。同心出版社、2016年版。
2022年3月22日、石中元撰文北京延庆淡泊湾书斋。